作者简介:
徐逸飞,1989年12月出生,上海人,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同时关注希腊晚期哲学以及柏拉图主义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哲学史中的演变。
摘要:本文澄清了普罗提诺《九章集》V3中努斯朝向太一并实现自身本质的学说,即太一如何生成努斯的论题。通过对两种思、两种现实性的区分,普罗提诺分别以尚未存在的努斯趋向太一的行为、出于实体的现实性以及太一与努斯内在的同一状态作为中介,构建出了一套从“单纯之一”到“多”的等级序列,借此太一在保持绝对超越性之时也能作为努斯及万物的原因。通过厘清以上几组概念的内在关系,本文将其回溯到一套全新的形而上学原则之上,借助区分两种原因澄清了一种特殊的因果性运作机制:原因以“非或前-原因”的方式作用于结果,而基于这种否定神学式的表述,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学说才能得到理解。
关键词:新柏拉图主义;太一;努斯转向;否定神学
引言
“流溢说”一直是众多学者赋予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理论标签。在通俗的讲法中,流溢论的体系由三种“本原性的本体”( )——太一、努斯与灵魂所构成,三者组成一种有着上下等级差异的一元论秩序。本文缘起于这样一组问题:在这种一元论框架之下普罗提诺如何理解太一与努斯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强调流溢学说的一贯性,那么太一必然要作为努斯生成的原因,努斯则作为流溢的结果。而如果基于太一的“超越性论证”,太一本质上不能拥有任何的规定性,当然同时也包括这种因果上的规定性,那么流溢说与太一的超越性论证如何相调和?绝对的太一如何同时又作为多的原因并产生出多?这种生成会不会摧毁它的绝对单一性?如果要回答以上的疑难,就必须深入地理解努斯生成学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原则。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以努斯的生成问题为入口,澄清这个核心原则。只有回到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够更完整地理解普罗提诺的体系,理解否定神学与流溢学说的内在一致性。
)——太一、努斯与灵魂所构成,三者组成一种有着上下等级差异的一元论秩序。本文缘起于这样一组问题:在这种一元论框架之下普罗提诺如何理解太一与努斯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强调流溢学说的一贯性,那么太一必然要作为努斯生成的原因,努斯则作为流溢的结果。而如果基于太一的“超越性论证”,太一本质上不能拥有任何的规定性,当然同时也包括这种因果上的规定性,那么流溢说与太一的超越性论证如何相调和?绝对的太一如何同时又作为多的原因并产生出多?这种生成会不会摧毁它的绝对单一性?如果要回答以上的疑难,就必须深入地理解努斯生成学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原则。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以努斯的生成问题为入口,澄清这个核心原则。只有回到这个原则我们才能够更完整地理解普罗提诺的体系,理解否定神学与流溢学说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如何理解这种“生成”?对此学界有着两种相对立的解释模型:反思式的与本原性的模型。这两派的思路建立在对《九章集》同一段文本(V1.7.4-6)截然不同的翻译与理解之上,原文如下:

读法一:那么它(太一)如何能产生努斯?通过太一转向自身,太一看到自身。而这种(自反式的)看本身就是努斯。
读法二:那么它(太一)如何能产生努斯?通过努斯转向太一本身,努斯看到自身,而这种(转向太一的)看本身就是努斯。
我们先来解释读法一。我们的翻译转译自拜尔瓦尔特斯(W. Beierwaltes)的德语翻译,他的译介很好地代表了第一种模型:“反思性的读法”。在这段文字中,他认为太一生成努斯就等同于它的自身反思,也就是说“转向”的主语和宾语都是太一,并且转向与生成是同一的,所以太一转向自身就等同于它生成了努斯。进一步他认为由于太一自身是单纯的,而这种朝向自身的太一包含着一种反思的结构,因此,这种朝向自身的过程就意味着一种从“绝对的一”向一种“包含差异的、存在着的一”的生成,这种包含着差异的“一”就是第二性的本体——“努斯”,它只有通过自反式的指向才能够与作为本原的“太一”相联系。
与其相反的是另一种模型:“本原性的读法”。这种读法中,主语是那个作为被生成物的努斯,宾语才是太一。努斯转向太一本身,而这种朝向太一的看才是努斯之活动。这种读法更契合于我们将要讨论的V3.11的上下文,同时也符合普罗提诺将思之活动排除出太一的一贯做法。笔者认为“反思性的读法”存在着如下的问题:首先,这个解释明显与其他许多文本相矛盾,在其他文意相似的文本中,主语都能较为清楚地被确定为“某种”努斯。其次,拜尔瓦尔特斯在这里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如果努斯尚未生成,太一又何以已经能够思?太一的自身转向就意味着作为自因去生成万物,而太一作为自因被新柏拉图主义所拒绝,因为它必然会摧毁太一的纯粹性与超越性。最后,如果我们强调朝向与生成的一致性,我们将如何解释“单纯的一”一定要转向自身,为何一定要变成与自身相异的他者?
然而,基于深入理解以上两个立场之间的相互辩驳,本文将提出第三种立场:“反思性的”及“本原性的读法”之间实质上并不构成义理层面的对立。两种读法为了规避自身困难所采取的辩护思路恰恰重合在了一起。“转向的主语”问题虽然在语文学意义上是可探讨的,但是终究在普罗提诺形而上学背景中是可相互置换的。本原性以及反思性读法的对立恰恰源自于对他形而上学总原则的含混不清理解之上。对于“本原性读法”而言,虽然它有效规避了太一从单一变为杂多的困境,但它引入了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也就是问句与回答之间随意的“主语转化”。该读法没有面对直接的问题,相反它产生了一种循环论证: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努斯或思维何以被生成,答案却是因为努斯思太一,这种思才是努斯,“思”同时作为了前提与结论。这个困境被支持“反思性读法”的学者频繁质疑。为了避免这种循环,“本原性读法”显然须被改进,也就是进一步区分努斯的两种含义:“尚未存在的原初努斯”与“已被生成的努斯”,因此V1.7的这段文本可以被理解为:尚未存在的努斯通过朝向(看、欲求)太一得以生成努斯。这也将更完美地符合我们所要给出的对V3.11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思”同时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循环被避免,在前提中是“原初的努斯”朝向太一,而结论中的努斯则是指“现实的努斯”的思维,同时太一也依然保有了单一性而并非陷入一种反思结构之中。这种改造本质上与阿多(P. Hadot)对反思性读法的改进异曲同工,稍显不同的只是他区分了“看”的两种含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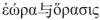 ),而非两种意义上的努斯,太一之“看”与努斯之“看”是双重现实性中第一、第二现实性相伴随的关系。按照这种解释V1.7的这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太一通过无区分意义上的“看”向自身产生了外部意义上的努斯对象性的“看”。严格来说,“转向”的主语“原初的、尚未存在的努斯”与“处在尚未被规定之看中的太一”两者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两种读法的对立在根源上就是不成立的。下文将细致考察在《九章集》中普罗提诺如何在同一个形而上学框架下对看与努斯作出双重意义上的区分,并且在此基础上解决“太一如何生成努斯”这一棘手难题。
),而非两种意义上的努斯,太一之“看”与努斯之“看”是双重现实性中第一、第二现实性相伴随的关系。按照这种解释V1.7的这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太一通过无区分意义上的“看”向自身产生了外部意义上的努斯对象性的“看”。严格来说,“转向”的主语“原初的、尚未存在的努斯”与“处在尚未被规定之看中的太一”两者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两种读法的对立在根源上就是不成立的。下文将细致考察在《九章集》中普罗提诺如何在同一个形而上学框架下对看与努斯作出双重意义上的区分,并且在此基础上解决“太一如何生成努斯”这一棘手难题。
一、对V3.11及其相关文本的翻译与解释——思的原初行为与现实之思的区分
在《九章集》之中普罗提诺反复讨论过太一生成努斯的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V3.11.1-18:
因此,只要当它想去思维超越者( ),也就是它想去将那一个(指超越者)当作一去思维之时,这努斯将会是多,而当它想去趋向作为单纯者(
),也就是它想去将那一个(指超越者)当作一去思维之时,这努斯将会是多,而当它想去趋向作为单纯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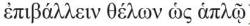 )的超越者之时,它得以出现(
)的超越者之时,它得以出现( ),与此同时它总是在把握(太一为)他物,此他物在它之中产生多。此种努斯就并非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努斯趋向超越者(
),与此同时它总是在把握(太一为)他物,此他物在它之中产生多。此种努斯就并非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努斯趋向超越者( ),而是作为一种尚未看到的视觉(
),而是作为一种尚未看到的视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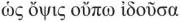 ),然而此视觉出离自身(或译离开太一)通过拥有视觉自身产生的多,如此它以不确定的方式欲求他物(
),然而此视觉出离自身(或译离开太一)通过拥有视觉自身产生的多,如此它以不确定的方式欲求他物( ),通过在其自身之中拥有它(太一)的印象(
),通过在其自身之中拥有它(太一)的印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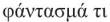 ),但它出现(或出离自身),是因为它把握了他物,此他物在其自身中产生了多。并且再者因为视觉拥有可见物的印象,此外视觉将不会允许印象在视觉中产生。
),但它出现(或出离自身),是因为它把握了他物,此他物在其自身中产生了多。并且再者因为视觉拥有可见物的印象,此外视觉将不会允许印象在视觉中产生。
但这种影像是出自一而是多的,并且努斯如此认识、看它(可见物),借此努斯成为一种看到了的视觉。一旦它拥有了这些,它就已经是努斯了,并且它是作为努斯拥有这些。而在此之前它只是一种欲求与尚未有形式的视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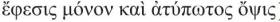 )。那么这个努斯趋向了(作为单纯者的)超越者(
)。那么这个努斯趋向了(作为单纯者的)超越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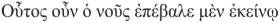 ),并且因为把握了它,努斯才生成,并且一旦它思了,此努斯就永远需要超越者并且成为努斯、实体及思维活动,因为在此之前它还不是思维活动,由于它还不拥有所思对象,亦非努斯,由于它尚未思 (
),并且因为把握了它,努斯才生成,并且一旦它思了,此努斯就永远需要超越者并且成为努斯、实体及思维活动,因为在此之前它还不是思维活动,由于它还不拥有所思对象,亦非努斯,由于它尚未思 ( )。(V3.11.1-18)
)。(V3.11.1-18)
在这段文字中普罗提诺刻画了努斯与太一关系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努斯通过朝向太一而被生成或实现自身的本质。理解这个论题的核心在于理解普罗提诺是如何区分两种思的。只有通过某种前思维的“尚未思的”思才能去“思”太一,进而,现实的思才能实现,因为此时努斯尚未被生成,那么在太一与现实的思维之间就还存在着一种前思维的意欲行为。
这段文本同样也是众多解释者所聚焦的核心,与我们的分析近似的是格尔森(Lloyd P. Gerson)与哈弗瓦森(Jens Halfwassen)的解释方案。他们在太一生成努斯现实的思维之前都强调了这种“前思维”的原初行为,哈弗瓦森细致地区分了太一生成努斯的双重层次(Zweistufen),并进一步将这种努斯前思维的原初行为(Urakt des Denkens)解释为柏拉图未成文学说中的“不定的二”,它作为多的本原(自身尚未是多),是一种原初的、蕴含着自身分裂的“一”,这种一也是一种尚未规定的二,它通过与“一”本身相结合来构成作为整体的、有规定性的“一-多”。(cf. Halfwassen, 2015, S.161-164)因此,在作为“多”的认识外物的思维与“太一”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自身二元化的“原初行为”作为中介。(ibid., S.163; 2004, S.88)埃米尔森(Eyjoólfur K.Emilsson)也做过类似的分析(cf. Emilsson, p.98),同时,他将这种“前思维式的对太一的经验”(pre-noetic experience of the One)理解为努斯与太一之间生成序列的中介,这种前思维式的经验提供了一种介于太一与努斯之间的“接触”( ),基于这种独立、特殊的原初的思或接触,太一与努斯之间生成上的因果关系才得以确立。进一步,他还指出了普罗提诺在思维与感性知觉学说中所做的类比,在对感性知觉的讨论中,感觉器官“接触”外在的刺激物对感性知觉的产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同样也适用于思的领域。在努斯“认识”太一的过程中,两者的“接触”表达了一种直接的同一性,并且换一个角度而言,这种认识就是太一生成努斯的过程。无论认识还是生成都建立在一种因果意义上的影像或表象式的连接(causal representational link)之上。努斯得以思太一的基础在于其本身就是一种太一的摹本或表象,在这点上普罗提诺显然追随了亚里士多德,因为他同样认为感觉与思都必须建立在一种对外在认识对象的印象(phantasia)之上。基于这些研究者的成果,笔者将逐行分析该段文本,以呈现普罗提诺如何将这种区分用于解释努斯的生成。
),基于这种独立、特殊的原初的思或接触,太一与努斯之间生成上的因果关系才得以确立。进一步,他还指出了普罗提诺在思维与感性知觉学说中所做的类比,在对感性知觉的讨论中,感觉器官“接触”外在的刺激物对感性知觉的产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同样也适用于思的领域。在努斯“认识”太一的过程中,两者的“接触”表达了一种直接的同一性,并且换一个角度而言,这种认识就是太一生成努斯的过程。无论认识还是生成都建立在一种因果意义上的影像或表象式的连接(causal representational link)之上。努斯得以思太一的基础在于其本身就是一种太一的摹本或表象,在这点上普罗提诺显然追随了亚里士多德,因为他同样认为感觉与思都必须建立在一种对外在认识对象的印象(phantasia)之上。基于这些研究者的成果,笔者将逐行分析该段文本,以呈现普罗提诺如何将这种区分用于解释努斯的生成。
首先,在第一段中普罗提诺描述了一种尚未被生成的努斯的一种原初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想要( )将超越者作为单纯者(
)将超越者作为单纯者( )去思考的意欲,这里的单纯者是普罗提诺用以对比后一阶段努斯的思维活动,也就是那种将对象作为自身的他物,或者说将对象作为与自己(思维者)相对立的被思维者去认识的活动,这两种活动在本性上是不同的,虽然这两者都可以类似地被称为一种“把握”(
)去思考的意欲,这里的单纯者是普罗提诺用以对比后一阶段努斯的思维活动,也就是那种将对象作为自身的他物,或者说将对象作为与自己(思维者)相对立的被思维者去认识的活动,这两种活动在本性上是不同的,虽然这两者都可以类似地被称为一种“把握”( )。但后者永远是将太一作为他者去把握(
)。但后者永远是将太一作为他者去把握( ),而前者则将太一作为自身去把握。在这种区分下普罗提诺在第二段中进一步补充论述:前一种“思”是尚未看见的、未有形式的视觉(
),而前者则将太一作为自身去把握。在这种区分下普罗提诺在第二段中进一步补充论述:前一种“思”是尚未看见的、未有形式的视觉( ),以不确定的方式(
),以不确定的方式( )去欲求。它描述了一种先于努斯思维实现之前的思,只是一种纯粹无规定的意向的状态,它单纯地意欲去把握某物,而不是在自身之中已经包含了一种确定的二元关系的思维结构(cf. Krämer, S.314),在VI.7.16.13中普罗提诺更直接地用“非思维式的观看”(
)去欲求。它描述了一种先于努斯思维实现之前的思,只是一种纯粹无规定的意向的状态,它单纯地意欲去把握某物,而不是在自身之中已经包含了一种确定的二元关系的思维结构(cf. Krämer, S.314),在VI.7.16.13中普罗提诺更直接地用“非思维式的观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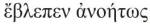 )表达这种前思维的意欲行为。这样,如果我们肯定了这两种“思”之含义的区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前思维地、非思维地”意欲去思的行为呢?要回答该问题,重点在于理解“
)表达这种前思维的意欲行为。这样,如果我们肯定了这两种“思”之含义的区分,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前思维地、非思维地”意欲去思的行为呢?要回答该问题,重点在于理解“ ”这个概念,这里笔者尝试将其译为“趋向”。它的原意可以被解释为:朝着某个目的投掷过去。如果在努斯这个层面运用,那么它指一种先于思维的把握行为,它指向“太一”但尚未理解“太一”。其实,这个词需要被放到一个更大的语意群中去考察,普罗提诺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词的词缀“
”这个概念,这里笔者尝试将其译为“趋向”。它的原意可以被解释为:朝着某个目的投掷过去。如果在努斯这个层面运用,那么它指一种先于思维的把握行为,它指向“太一”但尚未理解“太一”。其实,这个词需要被放到一个更大的语意群中去考察,普罗提诺运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词的词缀“ ”,他将多个具有
”,他将多个具有 词缀的动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意义群来解释这种先行于思维过程的原初行为,例如,接触、趋向、欲求(需要)、转向 。这些词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暗含着一种原初努斯与太一的同一状态,“接触”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是讨论“一”的时候的一种状态(cf. Metaph.Δ6, 1015b36-1016a17),同样“欲求”本质上是一种欲求者内在地拥有欲求对象之表象的状态。普罗提诺用这些词区分出了这种特殊的思维的原初状态。而且“
词缀的动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意义群来解释这种先行于思维过程的原初行为,例如,接触、趋向、欲求(需要)、转向 。这些词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暗含着一种原初努斯与太一的同一状态,“接触”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是讨论“一”的时候的一种状态(cf. Metaph.Δ6, 1015b36-1016a17),同样“欲求”本质上是一种欲求者内在地拥有欲求对象之表象的状态。普罗提诺用这些词区分出了这种特殊的思维的原初状态。而且“ ”不仅一方面有着同时伴随的意思,另一方面还有着一种趋向、指向的意思。例如指向太一(
”不仅一方面有着同时伴随的意思,另一方面还有着一种趋向、指向的意思。例如指向太一( )也就是说它同时意味着一种单纯的意向的状态。
)也就是说它同时意味着一种单纯的意向的状态。
与之相对立,普罗提诺对现实努斯的思维方式也作出了经典的描述:“它得以出现,与此同时它总是在把握(太一为)他物,此他物在它之中产生多。”(V3.11)这里的“它”显然指的是现实努斯的思维活动,而并非上一段中我们所讨论的“前思维的尚未生成的努斯”,这种思维活动在于将太一作为他物( )把握在自身之中,因此这种思在自身之中产生了多(太一自身与作为他者的太一),这样太一就被当作自身与他者对立关系中的一项而被把握。普罗提诺在这里运用了一种接近悖论式的表达刻画了努斯与太一的关系,努斯力图去趋向并把握太一,但如果这种把握实现为对象性的思,努斯实际上却是远离了(
)把握在自身之中,因此这种思在自身之中产生了多(太一自身与作为他者的太一),这样太一就被当作自身与他者对立关系中的一项而被把握。普罗提诺在这里运用了一种接近悖论式的表达刻画了努斯与太一的关系,努斯力图去趋向并把握太一,但如果这种把握实现为对象性的思,努斯实际上却是远离了( )太一,因为它只是把握了“多”或者在整体之中的一,而非单纯之一。这样,通过区分两种意义上的思,普罗提诺解释了未生成的努斯如何从第一种前思维的活动成为后一种现实的思,其中的核心就是这种前思维的意欲活动与太一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太一直接产生了努斯,而是要借助一种朝向太一的“意欲”行为作中介,“太一”才是拥有对象性思维的努斯的原因。那么在此框架之下,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已生成的努斯活动与太一的关系呢?普罗提诺回答道:努斯“通过在其自身之中拥有它(太一)的印象,它得以出现”。(ibid.)这个回答将努斯与太一安排进了一种有等级秩序的结构之中。
)太一,因为它只是把握了“多”或者在整体之中的一,而非单纯之一。这样,通过区分两种意义上的思,普罗提诺解释了未生成的努斯如何从第一种前思维的活动成为后一种现实的思,其中的核心就是这种前思维的意欲活动与太一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太一直接产生了努斯,而是要借助一种朝向太一的“意欲”行为作中介,“太一”才是拥有对象性思维的努斯的原因。那么在此框架之下,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已生成的努斯活动与太一的关系呢?普罗提诺回答道:努斯“通过在其自身之中拥有它(太一)的印象,它得以出现”。(ibid.)这个回答将努斯与太一安排进了一种有等级秩序的结构之中。
在引文第一段的结尾,普罗提诺用视觉上的例子来类比思维,在那里他所强调的是,视觉产生的唯一可能就是视觉拥有可见物的印象,如果没有这种印象视觉将无法发生。同样地,在被生成的努斯之中,推论性的思维活动要得以实现,也必须建立在一种印象之上。这意味着努斯必须要拥有一种“善的印象”即“与善同类”( )的东西,只有拥有这种相似性,它才能朝向太一、至善。按照上一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努斯的思维活动被理解为一种将太一作为他物(
)的东西,只有拥有这种相似性,它才能朝向太一、至善。按照上一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努斯的思维活动被理解为一种将太一作为他物( )把握在自身中的活动。同时,在V3.8中,普罗提诺界定了印象或影像的形而上学意义:印象或摹本就是一种在他物之中的原本,那么这里努斯所把握的“他物”就是作为原本的太一在努斯之中的印象。并且按照亚里士多德努斯学说的框架,思维者与所思对象在现实性上是同一的,那么被生成的努斯本身与它所把握到的印象都将是太一的摹本,通过这种方式他构建出了两者之间的上下层级秩序,并且在同一个原本摹本体系中加以讨论。
)把握在自身中的活动。同时,在V3.8中,普罗提诺界定了印象或影像的形而上学意义:印象或摹本就是一种在他物之中的原本,那么这里努斯所把握的“他物”就是作为原本的太一在努斯之中的印象。并且按照亚里士多德努斯学说的框架,思维者与所思对象在现实性上是同一的,那么被生成的努斯本身与它所把握到的印象都将是太一的摹本,通过这种方式他构建出了两者之间的上下层级秩序,并且在同一个原本摹本体系中加以讨论。
除了与原本之间的相似性,这种拥有印象的方式(即思维者将所思把握为自身他者的方式)还必然会导致努斯进入一种差异性、一种思维者与所思对象分离的结构,因为对于普罗提诺而言,努斯最本质的结构是一种对整体的意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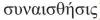 ),也就是将作为思维者的自我与作为思维对象的他者同时当作整体去意识(cf. Emilsson, p.97),这是一种对于整体之一(而非单纯之一),即自身作为思维者与同时作为思维者的他者(所思对象)所构成的整体的感知。普罗提诺在多处都提到过这种结构,在VI.7.39中,努斯的结构就是同与异之结合,在这种意义上,普罗提诺继承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关于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同与异的理念之结合的思想传统。这样努斯就绝不是太一,否则太一会变成复多之统一而非作为单纯之一的太一。在III8.9中,他也提到我们只能通过整体之一去理解单一,作为整体之一的努斯本质上是一种太一的摹本。所以说,只有当我们想要从努斯转向太一之时,我们才内在地拥有太一的印象(更准确地说,就是在他物之中的“太一”本身),那么努斯与太一才构成原本与摹本的关系,并且现实的、作为“一-多”的努斯才得以生成。
),也就是将作为思维者的自我与作为思维对象的他者同时当作整体去意识(cf. Emilsson, p.97),这是一种对于整体之一(而非单纯之一),即自身作为思维者与同时作为思维者的他者(所思对象)所构成的整体的感知。普罗提诺在多处都提到过这种结构,在VI.7.39中,努斯的结构就是同与异之结合,在这种意义上,普罗提诺继承了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关于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同与异的理念之结合的思想传统。这样努斯就绝不是太一,否则太一会变成复多之统一而非作为单纯之一的太一。在III8.9中,他也提到我们只能通过整体之一去理解单一,作为整体之一的努斯本质上是一种太一的摹本。所以说,只有当我们想要从努斯转向太一之时,我们才内在地拥有太一的印象(更准确地说,就是在他物之中的“太一”本身),那么努斯与太一才构成原本与摹本的关系,并且现实的、作为“一-多”的努斯才得以生成。
因为,这样一种单纯意向“太一”的趋向行为本质上是不能被实现出来的,当它实现出来之时只是作为一种思者与所思对立角度上的思。而前者永远伴随着后者,这个区分背后是一种太一本身与太一的影像之间的区分。尚未生成的努斯想要趋向太一本身,但最终把握的只能是太一的影像或摹本。这也是普罗提诺借用柏拉图式原本与摹本结构的缘由。原因对结果起作用的机制被彻底地改写了,普罗提诺(也包括与他思想上有着强烈亲缘性的中世纪“后继者”埃克哈特)区分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原因,它对于结果起作用的方式并非作为原因,而是作为一种“非原因”或前原因。这种非原因作用于它的第一个“结果”的方式是令它成为“自因”,从而实现一种因果上的传递性。
二、对V3.11努斯学说及其形而上学背景的解释——双重现实性学说的确立
我们稍稍离开关于太一如何生成努斯的文本,来检视一下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包括他的因果性学说是如何在努斯学说背后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由此就可以看到对“思”的双重含义的区分实质上是他形而上学讨论中一个必然的理论后果。我们首先从他对“现实性”概念的区分开始,普罗提诺认为一切现实性必须被区分为“实体自身的现实性”与“出于实体的现实性”。太一作为实体“自身的现实性”不直接产生多,而只是与“出于实体的现实性”相关联,两者之间是原本与摹本之间的关系,而现实的多的直接原因是“出于实体的现实性”。这样一来,双重现实性学说保证了太一并不直接生成多。这一点在V4.2.24-37中可以得到明确的文本支撑:
那么当那一个(指太一)作为所思对象保持(在自身之中),那被生成物就成了思维。而因为它是思维并且它思自身所从之而来的东西(即自身的本原),因为它并不拥有其他的东西,努斯因此产生了,似乎拥有一种相异的所思对象或似乎拥有“太一”,即一种太一的摹本或影像( )。
)。
但太一如何通过保持在自身之中生成(他物)?通过(出于实体的)现实性,(事物的现实性)一方面是实体自身的现实性( ),另一方面是出自于其实体的现实性(
),另一方面是出自于其实体的现实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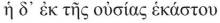 ),并且实体自身的现实性等同于它自身,而出于一切事物实体的现实性必定作为与其相异的东西跟随着它。正如在火那里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热,其完成了火的本质(实体),而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热已经出于火而生成,当火保持在火之中而实现其内在的伴随其本质的现实性之时,这种热同时也出现了。并且那里(指在太一那里)确实亦是如此,并且更是如此,那里太一保持在属己的本性之中,一种现实性出自一种在它(太一)之中的完善的、同在的现实性而被生成并获得实存(
),并且实体自身的现实性等同于它自身,而出于一切事物实体的现实性必定作为与其相异的东西跟随着它。正如在火那里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热,其完成了火的本质(实体),而另一方面也有一种热已经出于火而生成,当火保持在火之中而实现其内在的伴随其本质的现实性之时,这种热同时也出现了。并且那里(指在太一那里)确实亦是如此,并且更是如此,那里太一保持在属己的本性之中,一种现实性出自一种在它(太一)之中的完善的、同在的现实性而被生成并获得实存( ),因为它是出自伟大的能力,亦即一切万物之中最伟大的能力而进入存在与实体。(V4.2.24-37)
),因为它是出自伟大的能力,亦即一切万物之中最伟大的能力而进入存在与实体。(V4.2.24-37)
这两段文字的主旨还是在讨论太一如何生成努斯的问题,并且印证了我们的多点结论,即理解第一段中的论证核心在于:理解“它并不拥有其他的东西”这一表达。如果我们将“生成”学说的起点放在一个原初的尚未被生成的努斯之上,那么首先,作为一个尚未被生成者,它不能作为一个与太一相异的东西而存在,因此太一作为它的所思,只是作为保持在自身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努斯的他者( ),或者一种对象性的所思,后者将太一把握为他者,把它作为与认识者相对立的东西去把握。那么它思自身的本原,因为它不拥有与其相异的东西,太一与努斯存在于一种内在的同一性之中。所以,在第一段的结尾普罗提诺补充说明了努斯并非实质上拥有“太一”,而只是“似乎”,即在类比的意义上,拥有作为“所思对象”的太一。因为这种作为所思对象的太一只是“太一的摹本或影像”。那么如何理解这里努斯对太一的这种同一的、非对象性的拥有呢?
),或者一种对象性的所思,后者将太一把握为他者,把它作为与认识者相对立的东西去把握。那么它思自身的本原,因为它不拥有与其相异的东西,太一与努斯存在于一种内在的同一性之中。所以,在第一段的结尾普罗提诺补充说明了努斯并非实质上拥有“太一”,而只是“似乎”,即在类比的意义上,拥有作为“所思对象”的太一。因为这种作为所思对象的太一只是“太一的摹本或影像”。那么如何理解这里努斯对太一的这种同一的、非对象性的拥有呢?
第二段中普罗提诺用现实性学说重新解释了上述同一性,这种努斯与太一之间的同一状态指的是太一“出于实体的现实性”。首先对于一切实存着的东西而言,都有着两种现实性,“实体自身的现实性”与“出于实体的现实性”。例如太阳自身的光与其流溢出的光;火自身的热与其发散出的热。这两种现实性的前者相当于它实体的本质,而后者作为“相异的东西”必然伴随着实体的本质,后者从前者之中获得实存。也就是说前者作为原本,而后者是前者在他物中的现实性,因此作为前者的摹本。这种等同于实体自身的现实性所要解释的就是:在第一段中,尚未存在的努斯以“非他者”的方式拥有太一,而那种作为“相异的东西”伴随着实体的现实性,就是指思者与所思对象相对立的思之方式。
如果从生成的角度思考这组概念的区分,那么,太一表现为通过现实性(更明确的表达是通过“出于实体的现实性”)保持在自身之中而同时产生他物。通过这种作为中介的第二现实性(即“出于实体的现实性”),普罗提诺回答了太一如何在保证自身超越性的同时,又保有与万物之间因果性上的联系。因为,太一的第二现实性并不会导致一种太一与其生成物之间的直接关系,它的第二现实性只是给出了他物的实在。所以说其实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而是通过第二现实性作为中介,万有借由它自身的本质接收到了对于它自己而言的实在。好比说,太阳向外辐射,这是同一种活动性,眼睛借此看见了光,身体却借此感受到了热,光和热都是就接受者本质而言所能得到的实在性,是太阳的第二现实性,因为器官不同所获得的现实性也不同。因此,太一对万事万物的原因性地位并不建立在太一自身之上,相反只是建立在太一“出于自身的现实性”之上,而我们(努斯)与这种第二现实性有着一种内在的同一性,只有这种现实性才是对于我们而言的原因。(cf. Gerson, p.21)
而如果从努斯学说的角度来理解这组区分,可以说,尚未被生成的努斯前思维地朝向太一的活动就是太一出于自身的实体所流溢出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转向与生成是同一的。只不过,一个是以太一为起点向下的描述,另一个是以努斯为起点向上的描述。虽然,前者在普罗提诺那里是流溢说所讨论的主题,后者则属于理智与认识学说的范畴,但是按照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两者都只是普罗提诺形而上学框架下的必然理论后果。普罗提诺在许多地方将认识上的接触与生成上的因果依存关系相类比(著名的段落为VI8.18)。在那里,他论述了太一在某种意义上与努斯相接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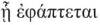 ),但事实上太一没有“自我规定”的结构,能够自我规定的只有努斯,只在作为努斯的意义上(
),但事实上太一没有“自我规定”的结构,能够自我规定的只有努斯,只在作为努斯的意义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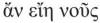 )才能说太一规定了自身的本质。对应因果性学说而言,太一相对于努斯并非一种必然的因(只能说是同名异义上的因),特别是,它不是努斯本质的必然原因,相反,努斯是以一种“自因”的方式规定自身的。对于认识学说而言,太一不能作为努斯直接的认识对象,在III.8.8.31的文本中,普罗提诺明确了即使是在尚未被生成的努斯前思维的把握中,它也不能将太一仅仅作为最单纯的一去把握,其自身已经包含了一种二元化。而相反努斯自身思维自身,自身给予自身规定性。(cf. Gerson, p.176; Halfwassen, 2015, S.165)太一并不直接生成努斯,也就是流溢学说概念的基本内涵必须通过一种“出于实体的现实性”为中介来作为存在的原因。
)才能说太一规定了自身的本质。对应因果性学说而言,太一相对于努斯并非一种必然的因(只能说是同名异义上的因),特别是,它不是努斯本质的必然原因,相反,努斯是以一种“自因”的方式规定自身的。对于认识学说而言,太一不能作为努斯直接的认识对象,在III.8.8.31的文本中,普罗提诺明确了即使是在尚未被生成的努斯前思维的把握中,它也不能将太一仅仅作为最单纯的一去把握,其自身已经包含了一种二元化。而相反努斯自身思维自身,自身给予自身规定性。(cf. Gerson, p.176; Halfwassen, 2015, S.165)太一并不直接生成努斯,也就是流溢学说概念的基本内涵必须通过一种“出于实体的现实性”为中介来作为存在的原因。
三、否定神学的基本原则——以非因作为因的因果学说
让我们将视角集中在普罗提诺这种独特的因果性学说之上。这种因果性学说来源于关于太一的著名“超越性论证”,太一作为原因必须是结果的超越者( ),这意味着因与果(太一作为因与从太一中流溢出的果)之间有着一种存在等级上的绝对差异性(
),这意味着因与果(太一作为因与从太一中流溢出的果)之间有着一种存在等级上的绝对差异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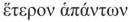 ),其著名的例子在V3.11.16-20中:
),其著名的例子在V3.11.16-20中:
那些东西(指一切存在者)的本原是先于那些东西(一切存在者)的,因为它们并不存在(于那些东西之中),相反一切存在者出自于它(存在),因为一切存在者所出自的东西不存在(于它们之中)。那这种一切存在者出自于它的东西并非个别物而是与“一切相异”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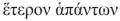 )。因此它不是一切(存在者)中的某一个,而是先于一切存在者的某个东西(
)。因此它不是一切(存在者)中的某一个,而是先于一切存在者的某个东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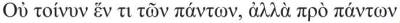 ),如此它也先于努斯。(V3.11.16-20)
),如此它也先于努斯。(V3.11.16-20)
在这个学说之下,一方面普罗提诺将这种特殊的因果性区别于一般自然物之间基于“相似性”( )的因果关系——就一般的自然物而言,相似的东西必须由相似者所产生(
)的因果关系——就一般的自然物而言,相似的东西必须由相似者所产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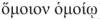 )。他笔下有着一个经典的例子:“火加热物体”,缘于某个热的事物的“热”加热了其他的事物,同时也令它们成为了热的事物。如果没有这种“热”之间的相似性,热在不同事物之间的“生成”与传递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典型的论述可见于V4.1.25。另一方面,不仅仅在自然物的生成与变化角度上,在理智认识活动的角度上,认识也遵循着这条“同形主义”的原则,认识也只能发生在同类之间。普罗提诺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同思维者与所思对象在现实性上是同一的,进一步而言,这种思者与所思对象在现实性上或形式上的同一是思维活动得以可能的基础。(cf. V3.7)
)。他笔下有着一个经典的例子:“火加热物体”,缘于某个热的事物的“热”加热了其他的事物,同时也令它们成为了热的事物。如果没有这种“热”之间的相似性,热在不同事物之间的“生成”与传递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典型的论述可见于V4.1.25。另一方面,不仅仅在自然物的生成与变化角度上,在理智认识活动的角度上,认识也遵循着这条“同形主义”的原则,认识也只能发生在同类之间。普罗提诺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同思维者与所思对象在现实性上是同一的,进一步而言,这种思者与所思对象在现实性上或形式上的同一是思维活动得以可能的基础。(cf. V3.7)
但是相对于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因果性,还存在着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因果性,在此因与果有着绝对的差别。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原因将没有任何规定性,因为这个绝对的原因恰恰要通过无规定性才能给出一切存在者的规定性。这种“无规定性”与“在先性”源自于一种绝对的差异性,并且普罗提诺通过这种差异性来理解绝对意义上的原因对于一切的“超越性”( )(cf. V4.2.37-42),进一步而言,这种无规定性甚至取消了它作为因的规定性。它是一种“先于、超越于因”的因(
)(cf. V4.2.37-42),进一步而言,这种无规定性甚至取消了它作为因的规定性。它是一种“先于、超越于因”的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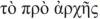 )。(cf. V5.9.7)
)。(cf. V5.9.7)
这种非因作为因的模式本质上来源于否定神学的基本框架:我们对太一本身不能有任何表述,如果对其进行表述,则表述自身就会成为一种悖论。“在一种意义上太一是本原,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并不是本原,……因为人们完全不能在与某物相联系的意义上诉说太一。”(VI8.8.9-13)因此,如果我们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述谓太一,那么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一种悖论式的表达:太一是非因之因、非本原之本原。在这里,拜尔瓦尔特斯对这种否定神学的基本原则给出了精彩的解释。他在评注中指出这种“非因之因”的表述背后是普罗提诺对于“否定”或者“非”的一种全新学说,这种太一与万物之间的绝对差异性同时意味着一种绝对的无差别性(In-Differenz),这种作为前缀的“无-”意味着一种生产意义上而非缺失意义上的否定(cf. Beierwaltes, 2001, S.146-149),是一种“充盈的无”(das Nichts als Fülle)。他借用爱留根纳的“双重学说”(duplex theoria)来解释这种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特殊的否定神学,即我们只有同时把握了太一与万物的无差别性与绝对差异性,才能够理解普罗提诺否定神学之“否定”的真正含义。这种绝对的“否定”也是对于太一任何肯定与否定式表述的同时谴除,这种同时性也意味着理智的、逻辑的矛盾律在描述“太一”时必定会走向自身悖谬。因此,这种“非因的因”在因果性领域中完美呈现了否定神学之“否定”的真正含义。太一要作为努斯的原因,只有在它“非”作为其原因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对太一生成努斯作出因果性角度上的刻画,我们只能双重地诉说太一既是努斯之原因,又非它的原因。这两者(因与果)之间有着绝对的差别性,同时也有着绝对的无差别性。
有了这层否定神学上的预设,我们进而可以回到努斯学说之中来对这种因果学说作一番考察。在努斯学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转向”( )概念,它的首要意义就是果对于因的一种回溯,这来源于结果对原因的一种依赖性,本质上也就是努斯对于其原因(太一)的一种欲求或者说需要。对于努斯转向太一的学说而言,它所解释的恰恰是否定神学,从否定的角度来解释原因概念。从否定神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以努斯为视角,我们才能够描述太一的生成或者流溢,因为对于太一自身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或者精确地说必然会陷入一种语言或知性上的二律背反之中。这种“尚未存在的努斯”对太一思维意义上的趋向(
)概念,它的首要意义就是果对于因的一种回溯,这来源于结果对原因的一种依赖性,本质上也就是努斯对于其原因(太一)的一种欲求或者说需要。对于努斯转向太一的学说而言,它所解释的恰恰是否定神学,从否定的角度来解释原因概念。从否定神学的角度来看,只有以努斯为视角,我们才能够描述太一的生成或者流溢,因为对于太一自身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不可能的,或者精确地说必然会陷入一种语言或知性上的二律背反之中。这种“尚未存在的努斯”对太一思维意义上的趋向( )同时意味着它从太一那里远离(
)同时意味着它从太一那里远离( ),或者说离开了与太一潜在同一的状态,而被太一生产出来,这种生成的因恰恰是不可趋向之非因。统而言之,尚未存在之努斯去朝向那本质上“不可被朝向者”,才是它从尚未存在的状态到被生成状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非因”,因为这种朝向的目的本质上是以“非目的”的方式而起到“目的”之作用的。这样,以一种尚未思的、尚未存在的努斯作为起点,我们验证了只有在“太一”的否定神学的基本框架中,新柏拉图主义式的流溢学说才有合法性。
),或者说离开了与太一潜在同一的状态,而被太一生产出来,这种生成的因恰恰是不可趋向之非因。统而言之,尚未存在之努斯去朝向那本质上“不可被朝向者”,才是它从尚未存在的状态到被生成状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非因”,因为这种朝向的目的本质上是以“非目的”的方式而起到“目的”之作用的。这样,以一种尚未思的、尚未存在的努斯作为起点,我们验证了只有在“太一”的否定神学的基本框架中,新柏拉图主义式的流溢学说才有合法性。
结语
通过在图表(见下页)中罗列出文中所梳理的不同概念及其平行关系,我们可以一窥它们相互之间如何隶属于同一个形而上学框架。在这个图表中,普罗提诺在不同行之间都作出了一种三元结构式的类比,可以说这个同一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最终任务是要去回答那个最终疑难:如果我们承认超越性 “太一”的绝对无关系性,那么它又如何同时能作为一切事物的因而与它们产生因果性上的联系?答案在于普罗提诺在太一与“多”之间加入了一种中介,进而组成了一系列三元式的秩序。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普罗提诺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思:尚未存在的努斯朝向太一的思与现实意义上的思,前者并不是一种有着思维者与所思对象之区分的思,而是一种去把握的单纯朝向、需求或欲求,在这种前思维的活动之中尚未存在的努斯与太一处在一种同一性之中。尚未存在的努斯在转向太一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实在性,这个过程也被描述为太一生成努斯的过程。在努斯实在性的意义上,生成与转向只是同一个行为的两个视角,努斯自身的本质则是由自身反思的结构所构成的,而非太一直接决定的。

其次,太一直接的产物只是存在作为存在本身或者说实在,而非个别存在者本质意义上的存在。在这种生成过程中,太一内在地与万物同一,这个同一的状态对应于努斯学说,也就是一种前思维的趋向行为。这种学说也包含在他的双重现实性学说之中,太一直接的产物是“出于实体的现实性”而非第二性的本体——已存在的努斯,而只是作为两者中介的尚未存在的努斯。
最后,这种非必然的生成给出了一种全新的因果运作机制,普罗提诺对“因”作出了双重含义的区分,太一之于努斯并非简单地作为因而作用于果,而恰恰是作为一种非因在起作用。可以说流溢说在最核心处依然是一种否定神学,两者在形而上学背景上是相互印证的。在这个基础上普罗提诺回答了,太一如何能既处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中,又处在一种绝对的不与他物相关联之中(即不在因果关系之中)。答案是“太一”以一种非因的方式作为因。这个答案的模式也导致流溢说并非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创造论或者目的论学说,第一本原并非作为绝对的因必然地生成作为多的存在者,也并非作为纯粹的现实性而是万物的目的因,相反只是作为一种非因或绝对的潜能优先于一切存在者。
【参考文献】
[1] Beierwaltes, W., 1991, Selbsterkenntnis und Erfahrung der Einheit. Plotins Enneade V3,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Plotin.Über Ewigkeit und Zeit (III7),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1, Das wahre Selbst. Studien zu Plotins Begriff des Geistes und des Einen,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2]Bussanich, J., 1988, The One and Its Relation to Intellect in Plotinus. A Commentary on Selected Texts, Leiden: Brill.
[3]Emilsson, E. K., 2007, Plotinus on Intelle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Gerson, L. P., 1998, Plotinus. Argument of the Philosophers, New York: Routledge.
[5]Halfwassen, J., 1992, Der Aufstieg zum Einen. Untersuchungen zu Platon und Plotin, Stuttgart: De Gruyter.
1999, Hegel und der Spätantike Neoplatonismus. Untersuchungen zur Metaphysik des Einen und des Nous in Hegels spekulativer und geschichtlicher Deutung, Bonn: Felix Meiner Verlag.
2004, Plotin und der Neuplatonismus, München: C.H.Beck.
2015, Auf den Spuren des Einen. Studien zur Metaphysik und ihrer Geschicht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6]Harder, R., Beutler, R.und Theiler, W. (hrsg.), 1990, Plotinus. Seele-Geist-Eines. Enneade IV8, V4, V1 und V3; griechisch-deutsch.Übers. von R.Harder, in e. Neubearb. fortgef. von R. Beutler u. W. Theiler, Eingeleitet, mit Bemerkungen zu Text u.Übers. u. mit bibliograph. Hinweisen vers. von K. Kremer,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7]Henry, P. und Schwyzer, H.-R. (hrsg.), 1964-1982, Plotini Opera, 3 Bän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8]Krämer, H. J., 1964, Der Ursprung der Geistmetaphysik.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latonismus zwischen Platon und Plotin, Amsterdam: Schippers.
[9]Szlezák, T. A., 1979, Platon und Aristoteles in der Nuslehre Plotins, Basel/Stuttgart: Schwabe.
原载:《哲学研究》2023年第12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4-2-18


